关于死的反思——兼为之唱一赞歌
萧乾(1910~1999),北京人,作家、记者、翻译家。有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,通讯特写集《人生采访》,散文集《萧乾散文特写选》,译作《好兵帅克》等。死对我并不陌生。还在三四岁上,我就见过两次死人:一回...
萧乾(1910~1999),北京人,作家、记者、翻译家。有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,通讯特写集《人生采访》,散文集《萧乾散文特写选》,译作《好兵帅克》等。
死对我并不陌生。还在三四岁上,我就见过两次死人:一回是我三叔,另一回是我那位卖烤白薯的舅舅。印象中,三叔是坐在一张凳子上咽的气。他的头好像剃得精光,歪倚在婶婶胸前。婶婶一边摆弄他的头,一边颤声地责问:“你就这么狠心把我们娘儿几个丢下啦!”接着,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。后来,每逢走过剃头挑子,见到有人坐在那里剃头,我就总想起三叔。舅舅死得可没那么痛快。记得他是双脚先肿的。舅母泪汪汪地对我妈说:“男怕穿靴,女怕戴帽。我看他是没救了。”果然,没几天他就蹬了腿儿。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,是当我失去自己妈妈的那个黄昏。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挣钱——地毯房发工资。正如我在《落日》中所描绘的,那天一大早上工时,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妈一宿浑身烧得滚烫,目光呆滞,已经不大能言声儿了。白天干活我老发愣。发工资时,洋老板刚好把我那份给忘了。我好费了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块五毛钱。我一口气就跑到北新桥头,胡乱给她买了一蒲包干鲜果品。赶回去时,她已经双眼紧闭,神志迷糊,在那里气儿哪。我硬往她嘴里灌了点荔枝汁子。她是含着我挣来的一牙苹果断的气。
登时我就像从万丈悬崖跌下。入殓时,有人把我抱到一只小凳子上,我喊了她最后一声“妈”——亲友们还一再叮嘱我可不能把泪滴在她身上。在墓地上,又是我往坑里抓的第一把土。离开墓地,我频频回首:她就已经成为一个尖尖的土堆了。从那以后,我就开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。
我的青年时期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度过的。死人还是见了不少。“八一三”事变时,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后身掉了两次炸弹,我都恰好在旁边。我命硬,没给炸着。可我亲眼看到一辆辆大卡车把血淋淋的尸体拉走。伦敦的大爆炸就更不用说了。
死究竟是咋回事?咱们这个民族讲求实际,不喜欢在没有边际的事上去费脑筋。“未知生焉知死!”十分干脆。英国早期诗人约翰·邓恩曾说:“人之一生是从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。”这倒有点像庄子的“生也死之途,死也生之始”,都把生死看做连环套。
文学作品中,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。它不是深渊,就是幽谷。但丁的《神曲》与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中的地狱同样吓人。英国作家中,还是哲人培根来得健康,他认为死亡并不比碰伤个指头更为痛苦,而且人类许多感情都足以压倒或战胜死亡。“仇隙压倒死亡,爱情蔑视死亡,荣誉感使人献身,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。”他蔑视那些还没死就老在心里嘀咕死亡的人,认为那是软弱怯懦,并引用朱维诺的话说,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,它同生命一样,都是自然的产物。“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。”这与司马迁的泰山与鸿毛倒有些异曲同工之妙。
死亡,甚至死的念头,一向离我很远。第一次想到死是在1930年的夏天。其实,那也只在脑际闪了一下。那是当《梦之谷》中的“盈”失踪之后,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船,经上海、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。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,海浪朝我不断龇着白牙。作为统舱客,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,我确实冒出过纵身跳下去的念头,挽住我的可并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。我只是想,妈妈自己出去佣工把我拉扯这么大,我轻生可对不起她。我又是个独子,这就仿佛非同一般。其实,归根结底,还是我对生命有着执著的爱,那远远超出死亡对我的诱惑。
只有在1966年的仲夏,死才第一次对我显得比生更为美丽,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逃脱无缘无故的侮辱与折磨。坐在牛棚里,有一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各种死法。我还总想死个周全、妥善,不能拖泥带水。首先就是不能牵累家人。为此,我打了多少遍腹稿,才写出那几百字无懈可击的遗嘱。我还要确保死就死个干脆,绝不可没死成反而落个残废。我甚至还想死个舒服。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尽:两口水咽下去,就人事不省了。那天下午我骑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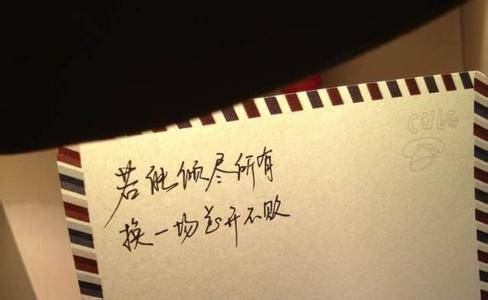


交流互动
发表言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