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“错”在独立思考
魏明伦(1941~),四川内江人,剧作家。著有《苦吟成戏》、《巴山秀才》等作品。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,往往出于好心,隐去鄙人阴暗面”,专讲幸运儿。仿佛是头沐春光,脚踏锦绣,一帆风顺走上...
魏明伦(1941~),四川内江人,剧作家。著有《苦吟成戏》、《巴山秀才》等作品。
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,往往出于好心,隐去鄙人“阴暗面”,专讲幸运儿。仿佛是头沐春光,脚踏锦绣,一帆风顺走上剧坛。有的评论者,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,熟悉舞台;比较了解我者,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,熟悉诗文;更具眼光者,发现我是个“杂种”——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,兼备两种“童子功”……。以上各有道理,本人甘苦自知,补充“交代”:我之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。基因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,不!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“独立思考”。
这个词儿,近年已无贬义;可在三中全会之前,在十年浩劫之中,在批判《武训传》之后,“独立思考”似乎是“脑后生了三根反骨”的近义词,谁沾上谁倒霉!我就因此铸成大错,误了前半生。
解放初期,我刚十岁,早已粉墨登场,小乖而已,绝非天才。只有两个优点: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,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。例如演出《潘金莲》,我扮郓哥,台前卖梨儿,台后捧着郭老的《少年时代》,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,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挂上钩来。异想天开,便去问我那搞编剧兼司鼓的父亲:“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,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?”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,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。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,只好去“独立”思考。据老师们说,我过早倒嗓,尖音一去不返,正是对这类问题“醒”得太早,想得太多的缘故。
性早熟无伤大雅,过早思索社会人生就危乎险哉。记得斯大林逝世,召开追悼会,奏起国际歌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没有神仙皇帝……”我的童心略感悲怆,跟着老师们默哀。忽然,有人放声干嚎,像麻五娘哭丧的“调门”!有人当场昏倒,像皇帝驾崩,臣民昏厥的“身段”!有人跪地叩呼“斯大林万岁”,竟与国际歌词发生尖锐矛盾!我的小脑瓜里迅速闪过一丝“独立”思考——这不是做戏吗?是表演啊!当时,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样反感,但都比我世故,不像孩子有感必发。我忍不住破涕为笑,两声哈哈,大逆不道!一位身穿黄军装的导演厉声斥责:“这娃娃没有无产阶级感情!”家父吓坏了,事后挥拳便打,我拔腿就跑,父亲穷追不舍,爷俩沿着剧场椅子兜圈儿……
现在回忆起来,我当时真不该笑,错了。可有些老师同志们那种“感情”是否属于“无产阶级”也须待考?中国的文盲艺人,对外国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,真情实感不多,悲戚则合度,昏倒则矫揉。那情景,与周总理逝世时,国遭大难,党处危急,人民切肤之痛,由衷之悲大不相同!后者真实,前者虚假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,建国初期变相继承,一些信徒把马列主义视为宗教,把苏联领袖供为佛祖,把追悼会开成近似迷信葬仪。不客气地说:更有人趁机“表演”以示信徒虔诚,意在给领导留下可靠印象,为入党入团创造阶梯!难怪咱们后来大跳忠字舞,盲从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培植了。
本人正因从小反感迷信,成年越发“思考”,所以屡罹文祸——一九五七年饱受批判,已够右派分子水平,幸而未到公民年龄,戴不上帽子,罚往农村劳动三年。“四清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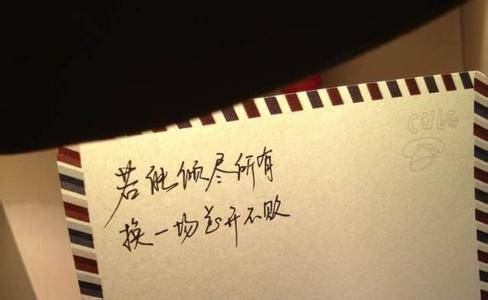


交流互动
发表言论